我所敬重的伍休武老师
伍休武先生是云南昆明人。1953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分配到天津工学院教书。
后因被错误地打成“右派”,安排到峰峰二中(现邯郸市第十四中学)教学。在校执教20多年,曾任副校长、校长,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市、省民盟副主委兼秘书长职务。
我和先生认识、交往这40多年来,一直称他为“伍老师”。老师的学识、才华、品德、人格魅力,使我非常敬重。
1962年,我正在峰峰二中上初中二年级。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,学校每天上四五节正课,每周还有一天的“劳动课”。组织学生做些种菜、喂猪、养鱼、帮厨、整修操场等活儿。有一天轮到我们班上“劳动课”,学校给我们几位同学派了一个任务,去彭城火车站接一位分配来的老师全家。我们拉着排子车赶到彭城火车站时,看见一位先生和一位清瘦的女同志,带着一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站在那里,便上前询问,果然是我们要接的老师。大家一齐动手,把老师带来的几件包裹和几箱子书装到了车上。
那时,从彭城火车站到峰峰二中,都是高低不平的土路。路上,伍老师和我们一块推着排子车。初次相识,大家在路上话语不多。但这位中等身材的老师,体态敦实,面容慈祥,戴一副眼镜,操一口云南口音的普通话,穿一身千千净净半旧灰蓝色中山装——还是深刻地留在了我的印象当中。
以这种方式和伍老师相识是一种缘分。我没想到,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师、班主任,成了我的至交朋友,成了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长者之一。
伍老师是我们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。上课时,他总是夹着一本书,提前到教室门前等候。铃声一响,走上讲台。他讲授高中课程的语文,造诣很深。在精辟地讲授课本知识的同时,还通俗易懂的灌输了很多方面的知识。一口云南口音的普通话,引经据典地娓娓道来,认真解答学生们的提问,不急不火,恰到好处。他讲课时,同学们的精力都很集中,大家静静地听着、记着。看到同学们渴求知识的目光,他有时也会发出会意的微笑。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,大家企慕敬佩。
每年的农忙季节,学校组织学生到乡村去支农。一去就是十天半月。带上被子,住到农民家里吃派饭,干农活。伍老师每次都跟同学们一块下去。一个家居南方,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,无论干什么活,割麦子、翻地、担水、栽红薯,都是带领我们抢着干,学着干。他经常和我们说:“劳动能锻炼人,体力上受点苦,但思想上是和劳动人民更近了。”
高中时,我爱好文科。他告诉我,除了书本上的基础知识外,要多阅读些课外书籍,多到学校的图书馆去。我记得,一些文学名著,历史、文化方面的书,都是这期间读了的。老师教我多读书,为我后来养成爱读书、藏书的习惯,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
我们那一届的高三年级,只有两个班(高25、26班)o在这之前,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不是很多。学校把打翻身仗的宝,押在了我们身上。学生们也憋足了劲,勤奋刻苦地备考,准备着最后的冲刺。
但是,这种梦想很快地破灭了。“文革”开始,高校停止招生。我们这些已经完成高中毕业考试,正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,便被挡在了进入高校学习的大门外。看着自己培养的学生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,伍老师更多的是感到了遗憾和无奈。后来,每当提起这件事,他总是非常惋惜地说:“耽误了一代人啊。”
在“文革”那样的政治气候下,学校停课了,书不能教了。他老实地接受着“改造”,接受着“再教育”,接受着“灵魂深处的革命”o我们偶尔相遇,也只是简短地相互问候。从他的眼神中,我看到了他的迷茫与不解。他个子不是很高,但他的脊梁骨是硬的。那段日子里,他没有哗众取宠,也没有取媚庸俗。无论受到怎样的批斗、诬陷,他更多地选择了沉默。他始终相信党,追求自己的信念。
1968年,我们分配工作。离开学校后,和伍老师见面的机会相对少了。但是,感情却更近了。老师关心离开学校的学生们。我们隔一段时间,就到学校去看望他。大家谈工作、思想、家庭、个人的事,听一下伍老师的指教。他学识广博,风趣幽默,和我们晤谈,彬雅和蔼,非常随意、亲切。每次大家都感到十分惬意,获益匪浅。
伍老师爱好广泛,业余时间爱写些古诗词,练练书法,搞些篆刻。他给人写条幅不多,亲自操刀刻印送人的就更少了。 1976年,我从彭城老家搬到了滏阳河畔的向阳楼家属院。他知道后,专门从云南捎回一个用细竹丝编织的精美挂幅。在上面用隶书写着“更上一层楼”、“送光华贤棣”等字样。我心里十分感激,深深地领会着他对我的期望、勉励、鞭策,这也成了我后来工作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。但看到他写的“光华贤棣”几个字,就有点受宠若惊了。不安地对老师说:“伍老师,你是我的老师,是我的长辈。怎么可以称我为‘弟’呢?”伍老师笑着说:“我们是好朋友,是‘忘年交’嘛,这里没有年龄距离。”话虽这么说,我仍然把他当成长辈,非常敬重他。他知道我爱看书、藏书,就用上好的石料给我刻过两方印。一方隶体“光华”印章,一方篆体“光华藏书”印章。治印苍劲浑厚,别有逸致。我一直在使用,并珍藏着。
我在区团委工作,经常去求教于他。我们谈工作、谈思想、谈家庭的事,也谈个人的生活。现在想起来,我后来的成长的道路,工作中取得的一点点进步,是离不开他的教诲和鼓励。我记得,在国家恢复高考后,青年中曾出现了一股学文化课的高潮。被文革荒废的心田,像禾苗一样急需用知识浇灌。区团委及时组织举办了函授大学学习班。从党政机关到基层单位,从中小学校到社会青年,中青年人报名者达到了几百人之多。找不到教室,就求助于学校的大教室。伍老师上下跑动地做工作,并被首聘于教授《古代汉语》、《现代汉语》课程。他欣然接受,热情很高。那时,没有任何报酬,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。他却乐呵呵地说:“看到你们年轻人都愿意学习,都愿意听我讲课,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报酬。”他每次讲课时总有几百人在听,大教室门外挤得满满的。那口含着浓浓乡音的普通话,展示着他渊博的知识和才华。在他的带动下,区里几个中学的有名教师,都参加了辅导教学工作。这件事,给当时参加过“刊大”学习的几百名学生,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
三
上世纪80年代初,伍老师众望所归地担任了十四中副校长、校长。后来,又成为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的兼职副主任。他的社会活动更多了,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
那时,伍老师经常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把十四中的优良传统传承下来。如何在新形势下,使它发扬光大,培养出更多、更好、更有用的人才。他结合学校当时的情况,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治校、育人的实施方案。一是在教师中狠抓师德规范,搞品德教育,提出了教师应学习、培养、提高的《十条修养》。从多个方面约束、规范教师行为,提高自身修养。二是对学校的校风,进行了概括、提炼,提出了在学生中要进行“朴实、好学、守纪律”的校风教育。伍老师认为,一个学校的好校风,是建校以来,广大教职工、学生共同培养和孕育形成的。保持好的校风,是学校各方面的工作不断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基础和保证。作为一校之长,他抓住了根本。一个学校教师的品德素质提高了,教学水平上去了,校风、校纪搞好了,这个学校还能搞不上去吗?他任校长期间,治校严谨,言传身教,身体力行,校风校纪为之一新,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赞誉。
伍老师上大学时,就加入了民盟组织,资格较老。由于民主党派工作的需要,为了加强健全全市民盟的工作,他被调往市民盟任副主委兼秘书长,并主持工作。民主党派恢复工作后,工作人员少,活动经费少,百废待兴。他与市民盟的工作人员,克服了不少困难,到各县、区调研,整顿健全组织,提出课题,向各级领导献言献策,获得了省、市领导的好评。市民盟的工作也多次受到民盟中央的肯定和表扬。有几次,我到市里开会,顺便去看望他,经常见他在那窄小的办公室内忙碌着,一会儿接电话,一会儿又安排别入去干什么,一会儿工作人员在汇报着什么,一会儿又来了客人,忙着接待。我给他打笑说:“伍老师,想着你找了个清闲差事,怎么这么忙呀?”他也不好意思地说道:“你来了,本想坐会儿说些话,你看就是这么忙,真没办法。”看到他精力充沛地忙活着,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快乐和甜蜜。
伍老师从河北省民盟驻会副主委兼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休后,家也从石家庄政协系统家属楼移居保定,和在保定市师专任教授的女儿伍晓晴居住在一个小区内,以便互相照顾。这几年,他上了年纪,旧时的腿痛病有时发作,行动不够方便。所以,往来邯郸、峰峰的机会就少了些。前几年,他回来几次,我们也相约到保定看过他几回。他精神矍铄,思想敏锐,谈锋仍健,非常地亲切、热情。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,但联系却始终没断,经常去电话问候。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给伍老师通了电话。问他和刘老师身体安康。问他最近干什么。他爽快地笑着说:“一天到晚忙得很,很少有时间出去。上午要看书3个小时,下午要看3个小时电视,晚上要上网2个小时。”他还说:“生命就这么多,我要过够、过好。"听着一个80岁老人的话,我本来很想说的一些话,一句也说不上来了……
我心里默默地祈祷:伍老师,祝你身体健康,生活快乐。
(作者曾任区委副书记,现任中国磁州窑文化研究会会长)
- 河北峰峰春光中学简史
- 峰峰春光中学建于2000年,是峰峰矿区第一所全封闭、全寄宿,16轨制,48个教学班的侧重升学预备教育的国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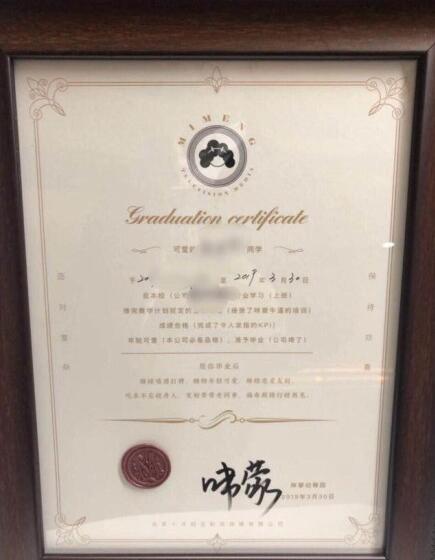 咪蒙公司解散了是真的吗,咪蒙公司为什么
咪蒙公司解散了是真的吗,咪蒙公司为什么 张靓颖乱入杨千嬅是怎么回事,左耳张靓颖
张靓颖乱入杨千嬅是怎么回事,左耳张靓颖 歌手2019第十二期突围赛排名出炉,2019歌
歌手2019第十二期突围赛排名出炉,2019歌 快乐大本营20190406期嘉宾彭昱畅沙溢胡可
快乐大本营20190406期嘉宾彭昱畅沙溢胡可 2019年峰峰民办幼儿园黑白名单 峰峰幼儿园
2019年峰峰民办幼儿园黑白名单 峰峰幼儿园 区长陈珍礼深入施工现场和企业一线夜查大
区长陈珍礼深入施工现场和企业一线夜查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