煤矿教育的拓荒者——刘彤录
2008年8月一个秋高气爽之日,我们前往省会石家庄去拜访原峰峰矿务局教育处处长刘彤录老先生。找到刘老的住处,一敲门,门应声就开了,一男一女两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探身出来。碰面话说罢,刘老指着老太太说:“这是我老伴老杨,也是从峰峰退休的老教师”。俩老人把我们让进屋里,就忙着递饮料、端水果。我们赶紧推让,刘老一瞪眼:“老家来的人,哪有客气的道理?”一句“老家来的人”,我们顿感热辣辣得亲切。刘老虽然肢体瘦弱身腰佝偻,却是精神矍铄,眉眼间充满了朴实慈祥,谈起往事,一路娓娓道来,悠然间,一个煤矿教育拓荒者的身影从我们心底升腾起来。
从保定到峰峰
刘彤录原籍河北保定唐县,生于1934年10月。 1954年7月从保定第二师范毕业,河北省教育厅统一分配师范生,他和14位同学被分配到河北省最南端的峰峰矿区任教。保定离峰峰800里,峰峰在哪个旮旯?是个什么状况?刘彤录全然不知,他和同学们捧着介绍信面面相觑,一片茫然。 7月10日,15个年轻人风尘仆仆来到峰峰,到区教育科换了信后,就有人分头把他们领往各校。刘彤录报道的学校是“峰峰矿区中学”,那时候,国务院正筹划把峰峰矿区改为峰峰市,区政府也酝酿着等改市后就把“峰峰矿区中学”改称“峰峰市第二中学”,虽然上头正式批文还没下来,学校里的师生早高兴得釜沸盈天了。有性急的学生索性自制成“峰峰市二中”胸牌戴上炫耀起来。其实当时的学校规模小得可怜,也就是十来个初中班。校园也是其貌不扬,主体教学楼正在建设之中,围墙之内到处是砖头瓦块、灰坑土堆。校址是跟黑龙洞村连在一起的,远远望去,学校也就像是在村边盖了个大院落而已。当时学校里连校长都没有,教导主任吴英荣就是最大的官儿。刘彤录报到后,被安置到第8班任班主任,并上两个班的数学课。教导处允许他第二天休息一天,备备课,第3天就登台讲课。带着一身保定尘土,又披上一层峰峰尘土,两地尘土一交融,刘彤录成了峰峰土地上的一名教师。此时,刘彤录刚满20岁。
刘彤录在峰峰二中干了两年后,因为工作出色,学校提拔他当了教导处副主任。就在他拉满弓弦欲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,突然一纸调令递来,叫他去筹办“峰峰市第三中学”,并担任该校的教导主任。年轻人拿着调令颠来倒去端详,他虽然想象不出筹建学校要遇多少艰难困苦,但是预感到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自己的肩头上了。时隔52年,刘老还清晰地记着,他接受使命的时间是1956年5月8日。
用脊梁扛起“峰峰三中”
接到调令的第三天,刘彤录来到“峰峰三中”上任。校址在峰峰矿务局机关西边的苍龙山脚下,几十亩的地皮上新建的校舍有的刚盖到屋顶,有的才垒到窗户台儿。要命的是满地长着半人高的杂草野蒿荆条子,风一刮,草丛中显露出一个又一个的坟墓堆。有位监工者得知刘彤录是来这儿当领导的,便凑过来开玩笑说:“刘主任啊,这地方叫谁来谁不来,你来了,你到这儿开荒来啦?”刘彤录放眼望望还是一片幻景的“峰峰三中”,淡然笑道:“开荒也总得有人干呀,这荒地不出来开,咋能变成沃土?”刘彤录话说得倒满有诗意,可他心里清楚,不拿出炼狱般的精神对付面前的这一摊子,荒野是变不成沃土的。
他在毛砖席顶搭成的“办公室”里安顿下来后,先召开了两个会:一个是全体教职工会,一个是党员会。那时候这野地上还没来校长,刘彤录就是“最高首领”。教职工拢共12人,有人戏称:正好是“一打”。全体会上,刘彤录除了鼓舞士气,再就是说了些安慰话。党员会上,他就没那么客气了。连他本人一共3名党员,他直言快语地讲:上级有指示,一是要在三月之内完成建筑任务并把必要的教学设备配备到位;二是要做好招生工作,9月1日如期开学典礼。这个硬仗是时间紧、任务重、困难多。咱们平时老喊“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”,实践与口号兑现的时候到了。就是脱层皮,咱也得把任务完成。仨党员神情凝重地表了决心,散会时把脚步迈得格外有力,好像将帅出征似的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刘彤录揣着自己制定的工作方案,领着他的“一打”军,超负荷地奔波、远转。清除杂草、联系迁坟、催动原料、购置设备、宣传招生,外带轮流值班防火防盗。其间有多少疲累辛苦、有多少次彻夜不眠已是说不清了。回忆起当年情景,刘老悠然一笑,幽默地说:“那可是在真正的‘原生态’环境中生活啊。夜间躺在床板上,能清楚听见西山下来的狼噢噢叫。有时候捉个野免子炖,没有佐料,光放上点儿盐。大家会餐手撕着吃,有人就说:“咱又回到原始社会了”。
8月下旬,校舍建筑如期完成,招生工作也基本就绪,9月1日按时开学典礼。那天,校园的黄土地平整洁净,新教室前放了几张课桌,周边零星插了些彩旗。典礼仪式首先要升国旗,没有旗杆,就栽了一根脚手架杆子。上午9点整,与会的上级领导和来宾全部到位,典礼开始。五星红旗冉冉升起,雄壮的国歌声中,“峰峰市第三中学”诞生了。刘彤录和全体教职工默默地流下了热泪。刘彤录代表学校讲话,却只字不提所经历过的艰辛,只是铿锵讲了几句今后如何工作的决心。刘老诉说着那时的场面,也给我们构勒出校园当时的面貌情形——空旷的黄土地上,一圈低矮的围墙。靠近东半部的地面上有序排列着30间青砖红瓦平房:4个教室12间,教职工办公室兼宿舍8间,库房3间,食堂联伙房3间,茶炉房l间,另3间是刘彤录的办公室,兼宿舍还兼学校会议室,剩余1间留给将来的校长。有趣的是,距这30间新校舍不远,居然还有五六座老坟堆突兀在那儿。原来坟主是“钉子户”,条件要得高,别的户都迁了,他却迟迟不迁。每逢上坟节令,这老坟的后代来祭典,青烟缭绕之中哭声袅袅,倒成了一道奇异的景观。这几座坟直到第二年才迁走。
学校是办起来了。当时“峰峰三中”的招生范围是二矿、五矿以北的厂矿和乡村,最远的与武安搭界,有十多里路。上学全是走读生。第一学期的前两月天不冷,学生还没啥动荡,可到冬天一下雪,冷了,教室里虽生了煤火炉,北风一刮里面还是阴冷得厉害,路远的学生有的就不来了。过了春节一开学,学生流失就更厉害了。有门路的往“一中”、“二中”转学,没门路的就不上了。统满招起的百十多个学生,眼瞅着稀哩哗啦就少了二三十个。要命的是有些学生家长还放出口风来:“那也叫学校?乱坟岗子上盖了几间房,还没有劳改队的条件好哩,能成啥气候?”刘彤录面对此情心焦如焚,他担忧学生流失的局面若收拾不住,这嫩芽似的“峰峰三中”就有刚开锣就塌台的危险。他心中的煎熬远比建校时多了十分。他锁着眉头琢磨,撑住危局唯有三条出路,一是改善办学条件“养住人”;二是深人家访以诚心“感动人”;三是以过硬的教学质量赢得信誉“聚住人”。第一项是远水解不了近渴,短期内指望不上,后两项还可行。刘彤录立马召开校务会,组织人员分头去做工作。印制《给学生家长的一封信》、到退学的学生家里走访、分批请学生家长来学校座谈,讲学文化的意义,讲三中的发展前景……这其间,附带着还给退学的学生宣布了一项承诺:再来学校坚持一学期,如果不满意,可随时退学。也就是说,来去可自由。别说,诚心的家访、别致的承诺还真管了用。想退学的学生不退学了,退了学的学生陆续回来不少。“退学潮”稳住了。就因这档子事,后来在峰峰地面上演绎出一句意味独特的顺口溜——“一中的球,二中的楼,三中学生最自由”。谁能想到,这“自由”二字的背后却是刻录着“峰峰三中”开创者们的爱心、诚心、雄心!至于教学质量如何,那就用事实说话了。 1957年夏季全区初级中学统考,峰峰三中的总成绩与“一中”、“二中”持平,有的科目成绩还胜过“一中”、“二中”。学校庆功会上,23岁的刘彤录感慨万千,他激动地对学生说了这么一句:我比大家大不了几岁,我这个老大哥愿意领着你们往前跑,只要咱们有信心、有毅力,学业就会更长进,将来就能成才。谁也不敢小看咱们!他给教职工们是这样说的:咱们用脊梁把“三中”扛起来了,咱们还要鼓足勇气继续扛下去,扛出信誉,扛出辉煌
1957年,峰峰三中曾经来过校长,但时日不长就走了,学校工作还是刘彤录扛着,他当着教导主任还兼任党支部书记。 1958年,三中划归峰峰矿务局管辖,学校改名为“峰峰矿中”。1959年,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干部来学校当负责人,他不大懂教育,对刘彤录说:“彤录呀,你就放开干,政治上我把关,业务上你该咋就咋。”
学校度过了“大办钢铁”运动,接着又熬过三年自然灾害。到了1961年后半年,才算平稳下来。这时候“峰峰矿中”办学规模比建校初期扩大了两倍。教师多了,难免就有这样那样的情况与矛盾。刘彤录对待教师的一贯态度是既尊重又重用,有的老师是戴着“右派”帽子调进来的,刘彤录不但不歧视,反而主动与他们交朋友,闲了拉拉家常话,偶尔喝点小烧酒儿,减轻他们的思想压力;奖金、福利、住房什么的也从来不苛扣他们。
事隔多年后,当年在三中工作过的老同志提起刘彤录仍翘指称赞:“老刘呀,那叫正派,在他手下干工作那是一种享受。”对老师中出现的纠纷,刘彤录也有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。面对风风火火的争执,他按下不管不问。只说:“先上课去。”然后夹上笔记本就去听他们的课。课讲得好,就表扬;讲得不好,先批评,然后坐下来亲切地商榷、指导。过了一段时间后,好像忽然记起他们闹纠纷似的,了解起矛盾的原由,然后把俩人叫一块儿,谁是谁非一评判,拿出公正的解决意见,不留“后遗症”o刘彤录把这一手叫做“缓冲处理法”。时日长了,老师们给刘彤录开玩笑说:“刘主任呀,你解决问题是‘曲线救国”’。1962年,邯郸地区教育经验工作会召开,刘彤录以《我与教师交朋友》为题作经验介绍,博得阵阵掌声。
六十年代初的峰峰矿中,论名气、论办学条件没法跟“一中”、“二中”比。刘彤录想把学校的文体工作促一促,开辟个亮点,可又无力购置器材。他一面向上级打报告申请拨款,一面就发动学生上西山割白草,秋收后到农田“拾秋”。聚了些资金添置文体器材,建起了文艺队、军乐队和体训队。刘彤录在保定二师上学时就是长跑健将,矿中建起体训队后,他自任赛跑教练。文体项目搞起来后,学校不定期举行竞赛活动,并组队参加峰峰矿区教育系统的各大赛事,各种奖项频频获取。峰峰矿中的文体教育教学从“无名之辈”成了异军突起,真正令人刮目相看了。 1963年,刘彤录撰写的《人人参加,层层负责,搞好学校文体活动》经验谈文章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,在峰峰乃至邯郸市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。
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,到1965年,矿中的教育教学质量达到高峰,那年的中考升学率达到98%,毕业生一部分考入高中,大部分考入全国各地的中专或技校。 9年卧薪尝胆,9年不懈追求,刘彤录当初把“荒地变成沃土”的愿望终于见到了曙光。面对收获,这个用脊梁扛起一座学校的年轻人,再一次流下感慨的热泪。然而就在学校步人辉煌的时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飓风呼啸袭来,刘彤录被打成“走资派”,靠边站了。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折磨落到他身上,他的脊椎被打成伤残,从此高度弯曲。直到今天,我们看到他弓着腰走路,上身一晃一晃的抖动,着实令人心痛。
有“战略胸襟”的教育处长
刘彤录从1966年6月“靠边站”,一靠就是5年。直到1971年春,他才恢复工作,被调到矿务局教育处主抓师资培训。“文革”动乱了好几年,全矿务局的教育事业受灾严重,有的教师被迫害致死.有的被打伤致残,有的调走,有的转行,还有的被遣返原籍,整个教育系统师资锐减、严重缺编。为解燃眉之急,教育处定了个措施:从高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,以“速成师范”的形式培训半年,然后充实到第一线。而具体工作就靠给了刘彤录。又是一个“临危受命”,刘彤录弓着脊梁扛起了这个重任。找培训场地、配教学设备、抽调培训教师、选拔参训学生……马不停蹄地费了一番周折,当年暑期就开班培训。他担任“教导长”还兼数学课。首批培训学员319人,结业之后分到各学校任课。72年、73年连着又培训了二三批学员500多人。大部分人到一线不久就独挡一面、胜任工作。以后的岁月里,这些学员逐步成为矿务局教育系统的中坚力量。直到现在,还有不少人或在领导岗位或在教学一线奋斗着。因为工作出色,刘彤录赢得了局领导的赏识,也赢得了广大职工的敬重。 1974年春,他被任命为峰峰矿务局教育处副处长,主管中小学工作。此时他40岁,正是不惑之年,按说,身为处级领导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,但当时的政治气候还处于“文革”之中,种种阻力制约着他,使他不敢放手放胆显身手。但是他已经在深沉地思考矿务局的教育事业怎么走下去这个“战略问题”了。他清楚地知道.“文革”之中,有大量工人“以工代干”进了教师队伍,其中有不少人根本胜任不了教学工作。“师训班”出来的学员虽然能胜任教学但毕业学历层次低浅。再就是各矿、厂学校的管理岗位上有不少是“造反派”发迹者或者是有“背景”而无才能者,这些遗留问题制约着全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提高,然而时机不成熟,这些问题还真是不能解决。 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文革结束,政治形势虽然变了,但“两个凡是”还在困扰。 1978年忙着扰乱反正、落实政策。直到1979年,刘彤录看到时机成熟了,这才把自己的“战略思想”付诸实践。他给处长谈了想法,形成一致意见后,汇报到局高层。不久,一个“整顿”方案就出台了。第一步先解决各学校领导班子问题,该拿的拿、该换的换、该调的调。选贤任能与惹人造罪并存,喝彩声与漫骂声同在,支持者与掣肘者都有。刘彤录已作好了思想准备:只要不撤我的职,骂也好,围攻也好,这路活儿我非干好不行。第二步全员培训,学历达标。对“以工代干”者,通过考试合格者留,不合格者退;对合格者,又以“速成师范”的形式补课培训然后上岗,并分批办了转干手续。对原来的“师训班”那几百人,则通过委培进修、函授学习、成人高考等各种渠道取得学历。在学校班子调整和教师队伍建设的“大换血”、“大改造”过程中,刘彤录费了多少心血,受了多少煎熬,那也数不清了。一年之后,全局教育系统的面貌焕然一新,而刘彤录的脊椎劳累得疼痛难忍,有时候只好靠着墙碰一阵才能坐下来办公。
1984年,刘彤录升任矿务局教育处处长,此后至1995年,他在教育处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1年。其间,他仍时时以“战略思想”考虑问题,拣主要的说:干了不少实事,诸如给教师争取假期奖金呀,给教师争取住房分配比例呀,给教师争取职称分配名额呀,一句话,凡是教师的合法权益,他都尽心尽力维护,并落实得有条有理。更干了不少大事,1986年各学校领导班子再次大调整,管理层进一步革命化、知识化、年轻化。 1989年调整教育布局,取消各矿学校的高中班,集中教育资源建立起“矿务局第二中学”(即今春华中学)o同时,还在五矿中学开办职业高中班。 1991年全局“普九”工作通过省级验收,成为“河北省普九达标先进单位”。此后至1994年,以“巩固普九成果,提高办学品位”为理念加强学校建设,实现了管理科学化、校舍标准化、设备现代化高标准的办学条件。这其间,刘彤录还有个宏大设想,要把五矿中学改建成一座高规格的职业高中学校,与“局一中”和“局二中”形成鼎足之势,为全局教育事业的发展筑起更厚实的基础。可惜职业中学这张蓝图未及实现,刘彤录已到了退休年龄,尽管局领导特批他缓退一年,但因种种原因,职业中学一事也未能如愿。至今刘老提起那桩“心事”,还遗憾得连连叹气。
1995年,刘彤录以61周岁的年龄从岗位上退休,退休之日,他特意到“峰峰二中”(今邯郸市第十四中学)和“峰峰三中”(今春晖中学)转了一圈儿。两处学校,前者是他初到峰峰的落足地,后者是他用脊梁扛起的创业地。观着眼前景,回想当年事,花甲老人感慨系之,禁不住热泪淌流。这热泪里徐徐回放着他41年来的身影与足迹。
- 河北峰峰春光中学简史
- 峰峰春光中学建于2000年,是峰峰矿区第一所全封闭、全寄宿,16轨制,48个教学班的侧重升学预备教育的国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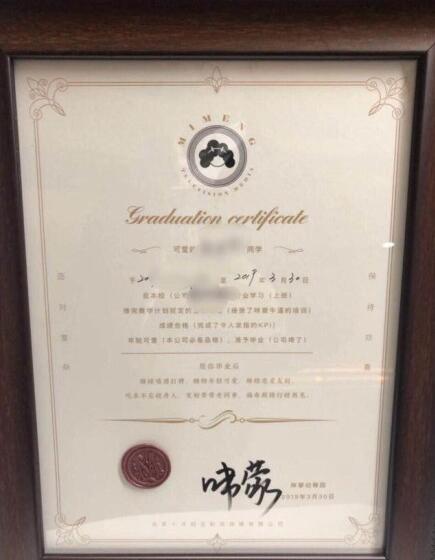 咪蒙公司解散了是真的吗,咪蒙公司为什么
咪蒙公司解散了是真的吗,咪蒙公司为什么 张靓颖乱入杨千嬅是怎么回事,左耳张靓颖
张靓颖乱入杨千嬅是怎么回事,左耳张靓颖 歌手2019第十二期突围赛排名出炉,2019歌
歌手2019第十二期突围赛排名出炉,2019歌 快乐大本营20190406期嘉宾彭昱畅沙溢胡可
快乐大本营20190406期嘉宾彭昱畅沙溢胡可 2019年峰峰民办幼儿园黑白名单 峰峰幼儿园
2019年峰峰民办幼儿园黑白名单 峰峰幼儿园 区长陈珍礼深入施工现场和企业一线夜查大
区长陈珍礼深入施工现场和企业一线夜查大